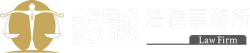一、案件背景:從家暴指控到刑事起訴
本案被告遭控於民國98年至105年間,對其女兒(下稱甲女)多次為妨害性自主行為。檢察官主張,被告利用父女關係,涉嫌對甲女進行猥褻及性侵行為,依刑法第227條及第228條起訴。
然而,案件牽涉時間長達七年,發生地點皆在家庭住所,無第三人在場。更關鍵的是,被害人於案發多年後才提出告訴,使得事證蒐集及舉證難度極高。
在此情形下,被告由我所李耿誠律師、曾偲瑜律師共同辯護,進行防禦策略。

二、檢方主張與起訴爭點
檢察官是依據被害人(甲女)陳述及其兄之轉述,認為被告自甲女未滿14歲起至成年後,持續以「父女關係」為機會,進行多次性侵及猥褻行為。
主要證據包括:
- 甲女及其兄之供述;
- 成大醫院精神鑑定書,內容提及甲女疑似有「非特定的創傷及壓力相關障礙症」;
- 檢方認為該鑑定可間接支持甲女之指訴可信。

三、辯護策略:以「證據不足」與「程序瑕疵」為防線
辯護團隊聚焦於舉證責任原則與合理懷疑原則兩大核心,從以下幾個面向展開辯護:
- 起訴事實不明確、時間模糊
起訴書僅泛稱行為期間為「98年至105年間」,並未具體指明每次性侵或猥褻的年月、地點、次數,甚至部分僅稱「要求」女兒行為,並未發生既遂事實。
法院因此認為,起訴內容不明確,難以確立犯罪構成要件。 - 被害人供述前後矛盾
甲女先稱被告「趁家人不在或睡覺時」實施犯行,後又稱「有時母親、兄長在家」。前後說法不一,且未能說明多年來家人為何全無察覺。
法院認為,其指訴存在重大瑕疵,難以採信。 - 補強證據欠缺
依刑事訴訟法第154條及最高法院判例,僅憑被害人陳述不足以定罪,必須有「補強證據」。
本案中:
甲女之兄僅為聽聞轉述,屬同一證據之累積,無補強效果。
甲女學業與社交狀況均正常,無任何行為或心理異常反應。
醫院鑑定雖指出甲女有情緒困擾,但距案發已十多年,且可能源於其他生活壓力或遭遇,不足證明性侵事件真實發生。 - 動機疑點:金錢糾紛導致報案
辯護人指出,案發前甲女曾向父親要求資助購車,遭拒後情緒不佳,隨即與兄長聯繫,並通報家暴中心。該通報紀錄明載:「因借錢遭拒,情緒不佳,方坦承過往事宜。」
此情節合理支持「報案動機非單純」的辯護方向。

四、法院見解:舉證不足,判決無罪
(一)第一審判決重點
臺南地方法院認為:
檢方未能提出具體犯罪時間、地點、次數;
被害人陳述內容有矛盾;
無第三人目擊、無生理跡證;
精神鑑定結果與案件關聯性薄弱。
綜合判斷後,法院引用「無罪推定原則」,認定「犯罪不能證明」,判決被告無罪。
(二)第二審駁回上訴
檢察官不服,提起上訴。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審酌後,全面維持原判。
法院指出,檢方上訴未能提出新證據,而被害人指訴瑕疵依然存在,精神鑑定無法證明性侵事實與心理創傷之間具有因果關係。
最終,上訴駁回、無罪確定。

五、律師觀點:刑事辯護的關鍵是「證據鏈」
本案顯示,即使涉及嚴重的家內性侵指控,只要檢方舉證未達「排除合理懷疑」之程度,法院仍會依據無罪推定原則,保障被告權益。
在刑事訴訟中,律師的角色不只是「辯護」,更是協助法院「釐清事實、檢視證據」的重要防線。
辯護重點包括:
釐清起訴瑕疵:檢方指控若模糊或矛盾,應立即主張程序瑕疵。
攻破證據鏈漏洞:確認證據是否具獨立性與關聯性。
心理鑑定的法律侷限:鑑定報告非屬直接證據,除非可明確連結行為與症狀,否則不能成為定罪依據。
舉證責任在檢方:被告無須證明自己無罪,只要證據不足,即應宣告無罪。
六、結語:當指控來臨時,正確防禦比沉默更重要
家內性侵案件具有高度敏感性與社會壓力,但司法審判的核心始終是「證據」。
如果你確信自己清白,應立即尋求專業刑事辯護律師協助,從程序、證據、動機等層面建立防線,才能有效對抗不實指控。